What Happens When You’ve Been on Ozempic for 20 Years?
GLP-1类药物的长期影响尚不明确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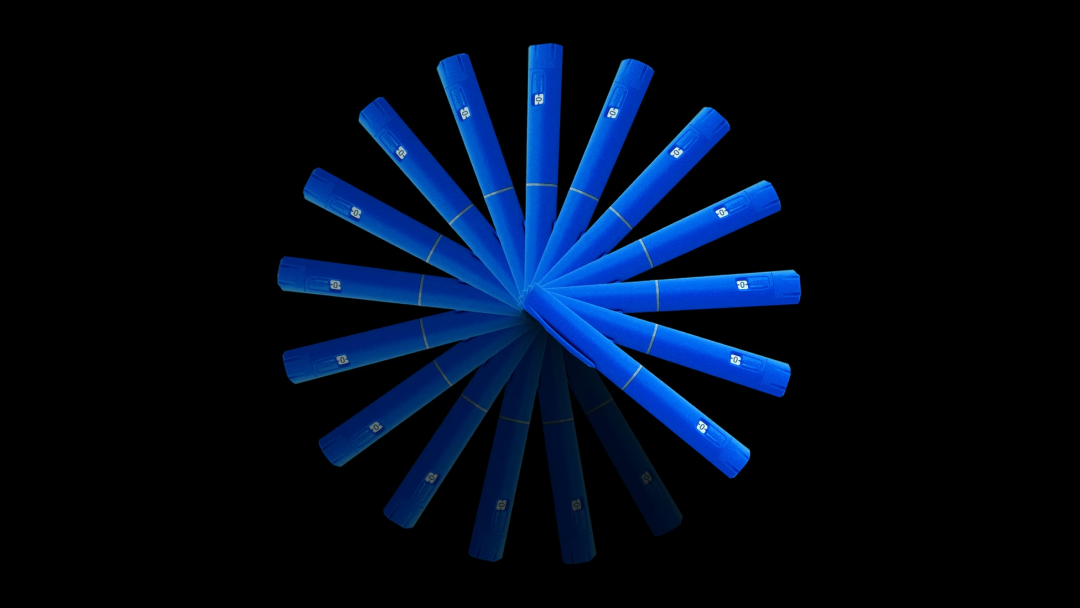
1921年12月,伦纳德·汤普森(Leonard Thompson)因身体极度虚弱、消瘦被送入多伦多综合医院,虚弱到需要父亲将他抱进医院。当时还不到十几岁的汤普森体重仅65磅(约29.5公斤),正处于糖尿病晚期。由于已没有太多可失去的,他成为了首个试用胰腺提取物的理想患者——这种提取物后来被命名为胰岛素。
胰岛素发挥了如今我们已知的功效。1922年3月,多伦多的研究人员与医生团队在《加拿大医学会杂志》(The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)上报告称:“这个男孩变得更开朗、更活跃,气色好转,还说自己感觉更有力气了。”文章记录了他们对另外6名患者使用胰岛素的过程,每一例似乎都实现了病情逆转。同年晚些时候,纽约罗切斯特的糖尿病专家约翰·威廉姆斯(John Williams)在描述他首位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时写道:“将这位患者恢复到如今的健康状态,其成就难以用平和的语言来描述。毫无疑问,医生见证过的从濒死状态下奇迹康复的案例,鲜有比这更令人震撼的。”
在医学史上所有“神药”中,胰岛素在功能与用途上,或许是最接近本世纪代谢类“奇迹药物”——GLP-1受体激动剂(胰高血糖素样肽-1受体激动剂)的。这类药物如今以人们熟知的品牌名销售,包括司美格鲁肽(Ozempic)、 Wegovy(均为司美格鲁肽制剂,适应症不同)和替尔泊肽(Mounjaro)等。它们是治疗糖尿病与肥胖症的新型药物,被誉为“一代人的突破”;正如《纽约客》(The New Yorker)在去年12月所言,未来或许能与胰岛素疗法一同跻身“慢性病史上最伟大的进展”之列。
但如果这个类比成立(且两者的相似之处确实不少),那么GLP-1类药物可能也会留下一份更为复杂的“遗产”。就胰岛素而言,它或许改变了医学领域,却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、非预期的后果。到1950年,在一家大型糖尿病治疗中心,这种新疗法已将患者确诊后的预期寿命延长了两倍。但与此同时,它也让患者得以存活足够长时间,从而经历一波长期并发症的折磨。伦纳德·汤普森最终在27岁时因肺炎去世;其他与他患有相同疾病的年轻人也过早离世,他们的血管被疾病严重侵蚀——或许(当时无法证实)也与最初维持他们生命的胰岛素疗法及相关饮食方案有关。
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,曾经罕见的糖尿病变得极为普遍,如今药店的整条货架都专门用于摆放糖尿病治疗相关用品。约有1/10的美国人受糖尿病困扰。尽管治疗药物与医疗设备日益丰富、不断发展,但无论是1型还是2型糖尿病,仍被视为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。患者的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,但病情仍被认为会随时间推移而恶化,需要更积极的治疗来控制其危害。如今,每7美元医疗支出中就有1美元用于糖尿病治疗,相当于每天花费8亿美元。
胰岛素疗法的出现还改变了——甚至可以说扭曲了——相关医学研究。在我的新书《重新思考糖尿病》(Rethinking Diabetes)中,我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临床研究者如何突然将重心从“理解饮食与疾病的关系”转向“药物与疾病的关系”。此前,医生治疗糖尿病时,要么采用“富含脂肪、不含碳水化合物”的饮食方案(这曾是欧美国家公认的标准疗法),要么采用“极低热量”的饥饿疗法;而后来,他们开始依赖胰岛素。医生们仍会坚称“饮食是治疗的基石”,但此时饮食已沦为胰岛素疗法的辅助手段,且他们默认患者不会遵行任何饮食建议。
如今,GLP-1类药物在这十年间迅速兴起,我担心类似的转变可能会再次发生。针对肥胖症与糖尿病的饮食疗法可能会被边缘化,转而青睐强效药物——尽管我们对这些新药的作用机制、以及它们能揭示的疾病本质几乎一无所知。即便这些药物的长期风险仍不明确,上述情况仍有可能持续。
《科学》(Science)杂志去年12月将这类肥胖症治疗药物评为“年度突破”,并在相关文章中指出:“围绕GLP-1受体激动剂的热情,夹杂着不确定性,甚至一丝隐忧。与几乎所有药物一样,这些‘重磅药物’也伴随着副作用与未知风险。”然而,鉴于GLP-1受体激动剂的惊人热度,这类警示往往听起来像是敷衍之词。毕竟,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已认定这些药物使用安全,且20年来医生一直在为糖尿病患者开具这类药物,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其存在长期危害。
但事实上,关于GLP-1受体激动剂副作用的深入研究,最长仅追踪至用药7年的情况,且研究对象使用的是艾塞那肽(exenatide)——这类药物中早期、药效远较弱的一种。该研究并未对试验中大量停药的参与者进行后续追踪。其他长期研究虽也对用药患者追踪了至少7年,但仅针对“胰腺癌、乳腺癌”等特定危害进行排查(且未发现关联)。与此同时,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,在因减重而处方新型GLP-1受体激动剂的患者中,超过2/3在一年内就停止用药。他们为何停药?停药后又出现了什么情况?
伦纳德·汤普森以及后来众多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的经历,或许是一种警示。GLP-1类药物与胰岛素有诸多共性:两种疗法都迅速风靡;胰岛素被发现后的几年内,几乎所有能获得该药的医生,都会为糖尿病患者处方;两者最初均为注射剂型,用于控制血糖;两者都影响食欲与饱腹感,且都能对体重及身体成分产生显著影响;与胰岛素一样,GLP-1类药物仅治疗其处方适应症的症状,因此,其疗效与胰岛素类似,需持续用药才能维持。
这两种疗法的相似之处还在于,它们均通过直接或间接调控极其复杂的生理系统发挥作用。在自然状态下(胰岛素由胰腺分泌,GLP-1由肠道——或许还有大脑——分泌),两者都参与“能量代谢与储存”的调节,即技术上所说的“能量分配”。这一系统决定了我们的身体如何处理食物中的宏量营养素(蛋白质、脂肪与碳水化合物)。
克里斯·福伊特纳(Chris Feudtner)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儿科医生、医学史学者与医学伦理学家。他将这种激素调控的“能量分配”机制描述为“食物利用委员会”。在《苦乐参半》(Bittersweet)一书中(该书记录了胰岛素疗法早期历史,以及1型糖尿病从急性病向慢性病的转变过程),他写道:“各个器官通过‘激素语言’相互沟通,身体其他组织则倾听这场持续的‘对话’,并根据激素信号的整体模式做出反应。随后,食物被用于燃烧、生长、转化、储存或提取。”若这种协调的“对话”被扰乱,整个人体的生理系统都会通过“纠正与反纠正”产生连锁反应。
这正是为何这些药物的长期后果难以预测。以胰岛素疗法为例,它不仅降低了患者的血糖,还帮助患者恢复了体重,随后又导致他们进一步发胖(即便它抑制了“极度饥饿”这一糖尿病失控时的典型症状)。胰岛素疗法或许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糖尿病并发症——例如动脉粥样硬化与高血压。这一可能性在教科书与期刊文章中均有提及,但从未作为科学结论得到证实。
随着胰岛素的发现及其治疗1型糖尿病的显著疗效,糖尿病专家开始信奉一种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治疗理念:用药物治疗疾病的即时症状,并假设未来无论出现何种并发症,都能通过其他药物或手术疗法来应对。例如,糖尿病患者若出现动脉粥样硬化,可通过支架延长寿命;若出现高血压,可服用降压药。
服用GLP-1类药物的患者可能也会面临类似情况(目前已有针对GLP-1相关肌肉流失的药物研发前景,这便是例证)。但这些新型肥胖症治疗药物的众多临床试验,无法(也不可能)评估“持续用药十年或更久”可能产生的影响,也无法评估“用药多年后必须停药”的后果。我们想当然地认为,即便在遥远的未来出现严重问题,或因副作用不得不停药,也会有新的疗法来解决这些问题,或替代它们维持体重。
与此同时,坚持治疗的年轻患者可能需要服用GLP-1类药物长达半个世纪。这几十年间可能发生什么?若停药(无论何时停药)又会发生什么?目前无人知晓——不过,说句可能不太吉利的话,我们终将找到答案。
孕期是另一个需要引发严肃关注的场景。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,与使用胰岛素的女性相比,在孕前或孕早期因糖尿病服用GLP-1受体激动剂的女性,其胎儿出现出生缺陷的风险并未升高。但出生缺陷只是孕期用药最明显、最易观察到的影响之一。患有糖尿病或肥胖症的母亲,其子女出生时往往体重更大,且成年后患肥胖症或糖尿病的风险也更高。孕期使用GLP-1受体激动剂,可能会降低——也可能会加剧——这种风险。若在孕前或孕期停药,母亲体重的突然增加(或反弹)也可能对胎儿健康产生类似影响。这些后果无法预见,且可能要等到这些孩子成年后才会显现。
GLP-1类药物的兴起,还可能像胰岛素疗法扭曲糖尿病研究思路那样,扭曲我们对肥胖症本身的认知。胰岛素被发现后,医生们假设所有糖尿病都是“胰岛素缺乏症”——但如今我们知道,这一说法仅适用于5%至10%的糖尿病患者(即1型糖尿病患者)。直到20世纪60年代,专家们才认可2型糖尿病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疾病:它是一种“胰岛素抵抗”状态,即身体对胰岛素敏感性下降,导致胰腺分泌更多胰岛素(而非分泌不足)来应对。如今,新确诊2型糖尿病患者的预后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,但医生们仍未明确:这种疾病的进展与长期并发症是否真的“不可避免”,或者说,这些后果是否实际上由“控制血糖的胰岛素及其他药物疗法”(甚至可能由“为配合这些药物而建议患者采用的饮食方案”)导致。
目前,人们已对GLP-1受体激动剂的作用机制做出诸多假设,但这些假设并未经过严谨验证以评估其有效性。人们普遍认为,这类药物通过“抑制饥饿、减缓食物从胃中排空”发挥作用——这些效果听起来无害,仿佛这些药物不过是“药理学版本的高纤维饮食”。但患者食欲与胃排空速度的变化,只是恰好易于观察和研究而已;它们未必能反映药物在体内最重要或最直接的作用。
我与克里斯·福伊特纳就这些问题交谈时,我们多次提到唐纳德·拉姆斯菲尔德(Donald Rumsfeld)对“局势不确定性”的经典表述:已知的未知与未知的未知。“这不是一种‘服用一次就能一劳永逸’的药物,”福伊特纳说,“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,一种新的维持疗法。我们必须与患者一同展望未来,帮助他们思考可能出现的一些后续后果。”
可以理解,患者可能没太多耐心听人罗列我们对这些药物的未知之处。肥胖症本身就带来了诸多负担——健康、心理与社会层面的负担。因此,在经历了一生的挣扎后,即便存在潜在风险,选择服用这些药物似乎仍是合理的。但历史告诉我们,医生与患者在权衡“已知益处”与“遥远未来的未知风险”时,应当保持警惕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