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当初享受拨号上网的人如今都已是中年人,在那个互联网初始的年代,智能手机还未出现,当时的手机只有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功能。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,是否还能记得当时的业余时间都是怎么打发的吗?
2000年,我入手了第一部黑莓手机RIM 957。它可以实时接收发送到我工作账户的电子邮件。一旦收到邮件,设备就会像传呼机那样闪烁灯光并震动。只要把它恰当地放在柜台上,震动就会通过石头和木头共振,把整个房间都震醒:有邮件到了!
有时候你能感觉到未来的阴影笼罩在当下——无形、冰冷,像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怪物。黑莓手机带来的感觉正是如此。它能够将数字事件注入到日常生活之中——哪怕你并不想要——这标志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开端:一个无处不在、持续在线的时代。
但当时还没到那一步。那时,主要是高管、政府官员,还有那些自认为重要的人才拥有这种新设备(我属于最后一类;我是做软件的)。我的同事们,尤其是我的妻子,都对这种“CrackBerry”(黑莓瘾机)以及我对它的痴迷感到厌恶,就像咕噜(Gollum)对他的魔戒那样。

© YouTube
接下来的那些年里,我一直在用带键盘的手机,直到最终被iPhone取代。我依然记得整个200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,在火车上使用Palm Treo、在午餐时使用黑莓的情景。但我却完全记不起,在此之前的那些年——在火车上、午餐时、或是在一天中任何的其他空闲时间——我都是怎么打发的。真的,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
有些事倒是容易还原。那时电子邮件是在办公桌前收发的,也就是说,你在午餐时间或离开办公室后是收不到邮件的。MapQuest(一款提供在线地图和导航服务的平台)已经出现了,但出门前必须先把路线打印出来。摄影还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因为当时还没有社交媒体可供发布。一些功能机虽然带有摄像头,但成像效果极为糟糕;而单独的数码相机价格昂贵,主要用于拍照后打印。
好吧,但人们到底是怎样填满那些如今被智能手机占据的时间、注意力和感知空间的呢?这个问题似乎很重要,因为智能手机的使用被认为是有害的。
过度使用常常被指责为导致焦虑、抑郁和强迫行为的罪魁祸首[1]——而几乎所有人似乎都在过度使用这些设备。智能手机还被认为让我们与世界、与他人之间产生疏离。人们不再享受午餐或旅游景点,而仅仅是拍照留念,为了获得也在使用智能手机的同伴的点赞。社会学家雪莉·特克尔(Sherry Turkle)曾哀叹,这些设备让人们过上了“孤独地在一起”的生活[2]。
我请一些中年朋友回想一下过去的生活,那时我们还真正“在一起”——然后告诉我他们是否还记得自己那时在做什么。“我那时候到底都在干啥?”其中一人反问道。一些童年的碎片还能被唤起:在车道上投篮、在课堂上传纸条、或者找朋友一起消磨时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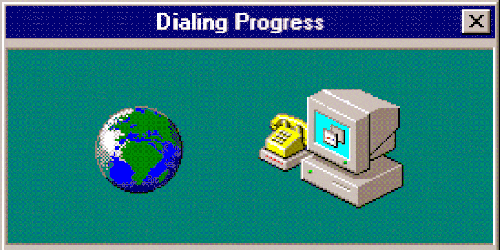
但作为成年人,我们闲暇生活的具体样貌却难以回忆。即便是早期的网络冲浪(当今刷屏行为的前身)也因为网速太慢而显得乏味。其他事情也都更耗时间:比如出门前得查纸质地图,买家电时要先找到销售员再当面咨询。至于那些日常里的“无所事事”——超市排队、堵车、遛狗——也都在与现在不同的情境中进行着,那时候的情况要更糟一些。

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是:我们之所以想不起自己当时在做什么,是因为那时根本没做什么值得记住的事。我们什么也没做,那感觉糟透了。
为了填补那种虚无,人们不断地用各种活动去占据时间。打电话是一种方法,虽然效果并不算特别好。那时,电话是人们远距离同步联系朋友的唯一途径。除了占线的代价或脖子酸痛之外,本地通话是免费的。在互联网出现并成熟之前,建议、想法和信息都不那么容易获得,所以你可能会打电话给朋友或商家,不仅仅是为了闲聊。

但当年的电话闲谈与如今的智能手机社交生活其实颇为相似。电话交谈也同样是媒介化的。人们打电话,是为了逃离家里或办公室里其他人的存在,就像如今人们发短信一样。电话通话既能填补空闲时间,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建立社会联系。而与此同时,这些通话也可能加重维系关系的负担,比如长途电话的费用,或者是想联系某人时必须打到他们家里、那根接在墙上的电话上。老式电话同样带来了思念与延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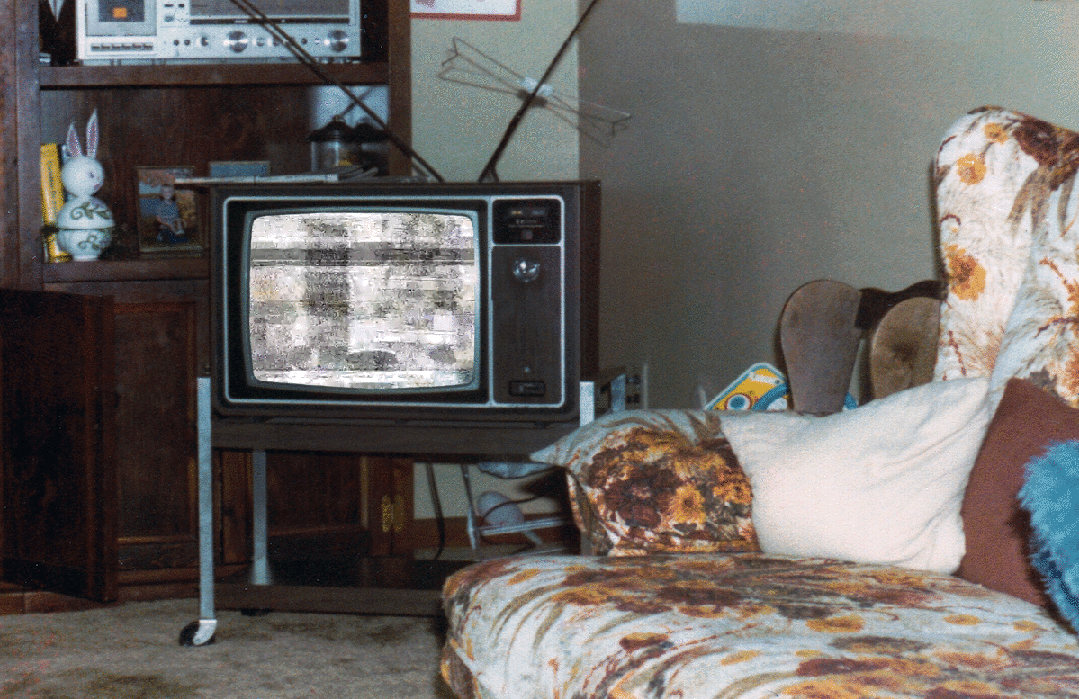
© Tenor
电视则是另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。我们看了大量的电视。游戏节目、白天的肥皂剧、情景喜剧、晚间新闻、MTV——电视几乎总是开着,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播放。只要人们在家,它就在播放。但在机场、诊所和自助洗衣店里也能看到电视。有些火车站和汽车站甚至在座椅扶手上装了投币式小电视,提醒着人们那种被困住时的绝望感。
我们还会通过翻阅报纸、杂志或商品目录来获取一些周边信息,就像如今刷手机一样。这些纸媒让我们在等待下一件事发生时,能看到一些新东西——哪怕只是随便什么。候诊室、飞机座椅背袋、公园长椅上都摆着杂志期刊。免费的周刊或分类广告报纸简直是天赐之物——比如在餐厅排队时,或者在汽车维修店苦等时。
如今我们刷手机消磨的空闲时光,当时人们是通过阅读一切可读之物度过的——垃圾邮件、地铁广告、麦片盒背面的文字、餐馆餐垫上的故事、调味瓶的标签。起初,人们嘲笑社交媒体:谁会在意你身边那些无聊的琐事呢?但在那之前,缺乏其他选择的我们,其实正是为了那些琐事而热衷。

© Harry Gruyaert / Magnum
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——在我们都拥有智能手机之前,真的几乎无事可做。你面前是一片空白的时间荒原:等公交、等人回家、等下一件预定的事开始。有人可能迟到了,或者比预期花更久的时间,但你不会收到任何延误的通知,于是只能盯着窗外,希望能看到街区尽头有什么动静。你会来回踱步,闷闷不乐,焦躁不安。
那种伴随着死寂时光的绝望几乎意味着,人必须以一种存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生命本身:荒诞、无意义,像是一片永远不会抵达岸边的倦怠之海。我们这一代人对无力感的偏好,很可能正是因为我们曾在极度孤独与无所事事中度过了太多时光。我们会读牙齿保健手册或洗发水瓶上的说明文字,会盯着时钟那平滑转动的指针。是的,当然,还有其他更好、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,但那只有在我们事先确切知道有多少时间、在什么地方、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浪费时,才有可能。而我们永远只有在为时已晚时才知道。
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,人们并不会利用这些闲暇时间去建立社会联系或进行自我提升。他们大多饱受无休止的无聊之苦。所以,让我们不要过分哀叹或谴责自己在智能手机上浪费的时间。被卷入争论或阴谋论、购物、欲望或无尽的负面信息流中固然不好,把工作带进牙医诊室或客厅躺椅里当然也很糟糕。但那种单调乏味的恐惧同样可怕。现在我们觉得信息太多、事情太多,但在那之前,唉,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